“杨红樱现象”似乎已成为中国童书界乃至整个出版界的一个专用名词了。这主要是因为她的作品畅销,而又被批评界视为艺术质量不高,并由此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双方,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代表着出版界(具体说就是出杨红樱书的出版社)和文学界(主要是一群坚持儿童文学立场的作家和批评家)。因为这样的书在
几年前的争端
最早对杨红樱的批评,也许出自阿甲发表于2004年8月25日《中华读书报》的《2004畅销童书过眼风云录》,是一种淡淡的点到即止的批评。文章在充分肯定《淘气包马小跳》的成功畅销,指出它在故事短小、插图丰富、贴近生活,并有浅浅的逗乐和轻微的教育意味之后,说了惟一的一句带有批评性的话:“虽然研究者或儿童文学爱好者可以从一些故事中轻易发现直接借鉴于其他经典儿童故事的段子。”同年9月22日的同一报纸,刊出了署名阿川的《原创童书真的没有一点独创性?》。凡涉猎过学术批评的人,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阿川将论争对象所说的“有”换成了全称的“无”。文中颇多“上纲上线”的话,最后将阿甲的观点点概括为“那就是国外的童书都比中国本土的强”,又是个全称判断,又是“都”。收尾的一句话是:“妄自菲薄可以休矣。”2004年11月17日,阿甲在同一报纸发表《我们应当呼唤怎样的畅销童书》,他没有回应阿川文章中那些上纲上线的话,但具体举出了杨红樱“直接借鉴”《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淘气包埃米尔》等经典童话的一些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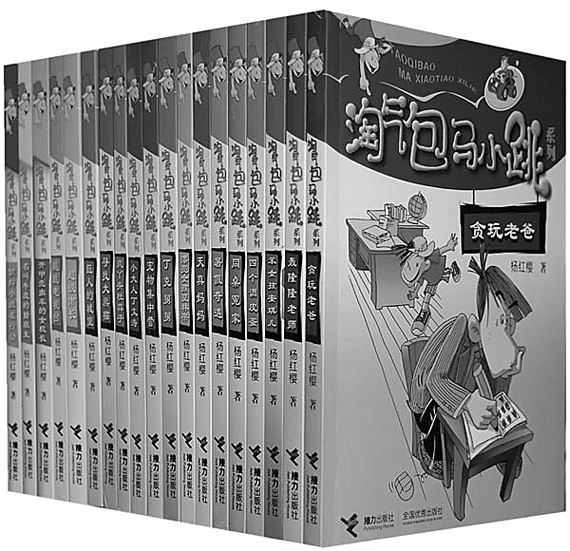
几乎在上述争论发生的同时,我写出了《试说杨红樱畅销的秘密》(刊2004年第4期《中国儿童文学》)。我在集中研读杨红樱作品后发现,她的创作严重缺乏文学性,但具备了一些搞笑故事特有的畅销因素(颇接近于《故事会》杂志中的笑话栏)。“这些故事从头至尾没有多少发展,除了马小跳年龄渐长,故事其实只有数量上的增加而已。”“既然这是从文学中剥离出来的畅销书,它因甩脱文学的羁绊而更为畅销,如我们还硬要将其作为文学来评述,甚至要把它树为文学的样板,那就不仅无理,亦复可笑了。”“打一个不伦的比喻,肯德基和麦当劳,够畅销了吧,但有谁会把最佳烹饪作品的桂冠,授给鸡柳汉堡或麦香鱼呢?这是两个向度上的追求。”
邱建果在2005年10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杨红樱不必郁闷》,对杨红樱的畅销模式作了充分的肯定。他的结论是:“我认为创作界历来就存在两种写作,一种是经典式写作,一种是商业化写作。我把杨红樱的写作总体上归为后者。”
2005年11月29日《中华读书报》报道了北京一次会议上曹文轩的发言:“有些人批评杨红樱,说她的作品格调不高……我认为,当下阅读生态的失衡,责任不在杨红樱身上。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完全有权利进行这种形态的写作。我觉得需要检讨的不该是杨红樱,而应该是整个社会。”
2006年5月李学斌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杨红樱”该不该挨骂?》,批评了我的上述文章和另一青年评论家陈恩黎的文章“都拿优秀、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来对比杨红樱的创作”。他认为,对不同作品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他提出有四种儿童文学:艺术的儿童文学、大众的儿童文学、商业的儿童文学和类型的儿童文学。而承认多元,正确归位,所有的纷争就可以“烟消云散”。
现在看来,我、邱建果、曹文轩、李学斌之间,有一点认识是相同的,即认为杨红樱作品无法与经典儿童文学相比(这正是我作对比和论证的目的);儿童文学界不必也不应对这样的作品“趋之若鹜”。至于将其归为哪一类,那还可作深入讨论(我觉得李学斌的四种分类还存在缠夹,如“类型”与“商业”、“大众”之间就有明显重叠)。当然,也有论者对杨红樱作出了极高评价,李学斌文中就引用了白冰的话:“‘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是艺术含金量、文化含金量、市场含金量三者统一的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白冰文章尚未见,权将此话聊备一格。
2004年底,由团中央等七部委联合发起“未成年人发展论坛”,在上海分论坛的发言中,方卫平首次提出目前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正处于低谷,我在发言中作了响应,并作出进一步的论证。许多媒体对此作了报道。12月26日《新民晚报》在“谈话”版刊出了会上发言,我名字下有这样的话:“儿童文学创作正处于近年来最低落的状态。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出现特别重要的作品,也没有多少新人涌现。少儿出版中的所谓畅销书,主要是两种:简单搞笑的系列书(如杨红樱的作品)或成套推出的‘青春文学’(其实是写得相对干净的通俗软性读物),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
至2005年夏,情况仍未有根本的改变,童书出版物在上述两方面的跟风克隆有愈演愈烈之势。9月中旬,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作家彭懿指出:“刚刚结束的少儿图书订货会上,一眼望去,花花绿绿的几乎全是杨红樱的书。”“杨红樱的图书是畅销书,充其量只能是读物。我们不是要贬低杨红樱的书,但是,杨红樱几乎占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半壁江山,一个人的创作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占有如此地位,这到底是好事还是一种悲哀?”我则重述了半年多前的看法,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目前已经陷入最低谷”。9月20日《新闻晨报》对此作了报道。
这些发言很快受到反击。在北京的一次会上,樊发稼“怒斥上海某些评论家无视儿童文学近些年来的进步,认为在他们眼中,国外月亮就是比中国圆,是自轻自贱”。(见2005年11月29日《中华读书报》)并把他们称为根本不读作品却妄下结论的酷评家。12月20日《文艺报》发表李东华的文章《2005,儿童文学的新声音》,文章一开头就说了一段与樊发稼几乎一样的话:“2005年的儿童文学是沉稳的……不像一些不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就敢妄下断言的酷评家所说的,我国儿童文学正处于低潮。”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年以前,阿川在批驳阿甲时,一开头就说的话:“阿甲先生是‘卖书人’、‘爱书的读书人’、‘阅读推广人’,也许是平时事务太多,加之童书又是‘相当初级的’,阿甲先生没有时间细读,或者是不屑于细读,他对原创童书所作的评判在我看来显得轻率和不负责任……”值得想一想的是:为什么一有人提出批评,马上就要断言他是“根本不读作品”或“没有时间细读”?这样说有根据吗?难道读了作品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不能有与自己稍稍不同的见解?
关于童书评价体系的论争
2008年秋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一个有关杨红樱作品的研读会。在所有新闻中突出报道的,多为浙江少儿出版社副社长郑重的发言。《中华读书报》10月15日头版,刊发了题为《杨红缨引发书业界反思童书评价体系》的会议新闻,主要内容是郑重和北师大教授王泉根对杨红樱的评价。报道中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推论。比如,郑重说:“在职业的出版人看来,如果作品不具备内在的特质,即使花十倍以上的推广力量,也不可能获得畅销;即使内容尚可的作品,在推广上不惜血本可让其畅销三五月,但绝不可能像杨红樱作品那样,畅销三五年甚至整个2000年代。”于是他认为,“断言杨红樱的畅销仅是‘商业化的畅销’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很奇怪,为什么畅销时间一长,性质就变了,就不能再说是“商业化的畅销”?商业化就只能“三五月”?这是不是受了中国图书大多短命的影响?事实上,畅销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商品有的是。就说咖啡吧,现在八十岁以上的人,有很多都能记得儿时听到过的麦氏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的广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难道这种咖啡已不是“商业化的畅销”,而真的转化成伟大精神产品了?真正的畅销肯定要有“内在的特质”,靠人为硬做出来当然不行,但这是什么特质?还不就是畅销的潜质,亦即商业化的特质吗?
当然,书业界有“畅销”和“长销”的说法,但概念的转换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何况杨红樱的畅销记录并不是指她哪一种书,而是她历年所写各种书的总和,所以,说“高产加畅销”,也许更准确些。
 王泉根教授说得更实在,他的开场白是一个实例:“前不久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上,一位民营书店经理说:‘杨红樱三年不写书,我们卖什么?’”这太说明问题了:作者快写,出版社快出,零售商快卖,这不正是典型的商业行为吗?
王泉根教授说得更实在,他的开场白是一个实例:“前不久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上,一位民营书店经理说:‘杨红樱三年不写书,我们卖什么?’”这太说明问题了:作者快写,出版社快出,零售商快卖,这不正是典型的商业行为吗?
应该说,杨红樱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拉动了中国童书的出版和销售,这是一件大好事,零售商和出版社感谢她,更是无可非议。然而,因为她商业上的成功,就一定要“反思童书评价体系”,要承认她的作品是“优秀的儿童文学”,要文学批评界改变“评价标准”,这就有些荒唐了。我甚至觉得,其荒唐程度不亚于一个人当了总统就一定要高等学府授予他名誉博士学衔。事实证明,这些出版者对于过去有的评论家(比如邱建果、李学斌等)把杨红樱定位于“商业化写作”是并不满意的,它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将其树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样板”。
其实,商业上的成功,与作品文学性强不强,本来就是两回事。文学性要通过艺术分析来把握,商业成功要通过市场来把握。想通过市场来把握文学性,是不可能的。市场上畅销的书既有文学性强的,也有正好相反的,这一点也不奇怪。文学性并不是畅销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可以怀疑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有问题,但你还是要通过更有说服力的、更深入作品实际的艺术分析,来取代那种过时的不合理的批评,而不是借用市场上的成功来说事,更不能用零售商要货的话来取代艺术分析。对《哈利・波特》那样的作品何尝不是如此?谁也没有因为它的全球畅销就说它文学性强;我倒是写过赞扬它文学性的文章,我用的也还是艺术分析,并不与它的畅销混为一谈。但面对商业性和文学性都远不能和《哈利・波特》相比的杨红樱的书,出版者却提出了非分的要求。
郑重有这样一段话:“为什么在严肃的儿童文学评论体系指导下,作家们并没有写出很受欢迎的作品?而能让亿万小读者疯狂着迷的作品却恰恰受到主流评论界的批判?”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批评家并不能指导创作,创作是作家的工作。批评总是第二性的,批评家的作用小得很,他只能在创作发生后,作一些分析而已,也许相当于化验师吧。通过投入的审美体验和艰苦的论证(其中包括对大量作品和过去的审美经验作细致比较),发现作品的美点和独创性,指出它艺术含量的高下,当然也可指出由艺术所表达的思想的含量,这就是他的工作。提醒一句,那些不以艺术分析为基础而经常下一些空洞的大结论的批评家,往往是可疑的;那些自以为是创作指导者而爱在作家面前指手画脚的批评家,更不要轻易去相信。或者也可以说,批评家相当于品酒师,你不能因为没有酿出好酒,就迁怒于品酒师的存在。你也不必因为品酒师说你的酒味不醇,就怒不可遏。他公布的不过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你完全可以设法把酒味搞得更好些。如果一桶酒卖得很好,而品酒师说不好,也不要一定以为是品酒师的错。他有自己的工作准则和工作尊严,他的工作具有独立的性质,他不是你的推销工具。很可能有些品酒师为生产商所买通,什么酒都说好,但这样的人总是长不了的,因为他已沦落为酒商的跟班。
既然有不同的打分,就有人爱判定对错。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现在的很多人,总以为市场是第一的,或惟一的:什么东西,市场好,一切好;与市场有矛盾,那一定是另一方的错。这种思路的实质,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批评的“金钱至上”和“金钱万能”。上海作家孙?在一次发言中说,现在对于金钱至上的批判太不够了,甚至还不如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们。这一提醒非常及时,简直可说是如雷棒喝。因为商业的需要,就希望文学批评能改变声音,这事实上是要将批评纳入整个商业运转中去(就像现在有的批评家正做的那样),这种非分之想正是金钱至上的典型表现。
“商业童书”的来临
我发现,在此之前,我们其实并没能对杨红樱的作品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它代表着一个新的事物,这是随着书业的高度市场化,随着出版社的改制而到来的。它的最合适的名称,应该就是商业童书。
本来,儿童文学都是为儿童而创作的,是“为了儿童”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起点一致。市场经济到来了,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在成人图书领域,出版了大量纯为盈利的商业性书籍;在舞台演出中,出现了大量奔着钱而来的商业性演出;在童书出版业,商业童书也悄悄萌生了。它以三阶段进入人们的视野:
第一阶段,在一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畅销的因素,它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作家也保持了自己的责任心,但市场和出版社很快发现了它们的商业价值,《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就是这样的作品。
第二阶段,作家和出版者都开始以畅销为目的,采取了各种“走市场”的方式,但在作者们的心目中,仍丢不开对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追求,也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责任心,所以作品常呈现矛盾和分裂的状况,水平参差不齐,畅销程度也受限制,曾经很活跃的“花衣裳”组合就是这样的作品。
第三阶段,作家和出版社密切配合,调动一切营销手段,从创作阶段起就进行包装,推出了一批艺术品质粗陋但轻松可读的书籍。所谓审美价值和责任心事实上已被扔在脑后,畅销和盈利成了主要目标。到这个时候,“商业童书”正式登场,杨红樱的“马小跳”系列是它出现的标志。杨红樱,成了中国商业童书的领跑者。
当然,商业童书并非全无艺术性可言,甚至,它也未必没有一点教育性。但在它们身上,艺术性和教育性,都成了商业的工具,都是作用于畅销的元素,而真正的目标是快速盈利。目标变了,整个性质也变了。
不妨作一类比:那些此伏彼起的商业性演出,难道没有一点艺术性可言?刘德华、费玉清、蔡琴的歌,有时艺术性还是很强的,甚至也有对人生的咏叹和规劝,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商业演出的性质。杨红樱作品的艺术含量,与蔡琴、费玉清比一比,是更高呢,还是更低?每个人都可作出掂量。
对于商业童书,我们还来不及作出更多的研究。但至少有一点界限,可以先予划清,那就是:畅销,不等于文学性强,不等于艺术性强,更不等于思想性强,也不等于教育性强;只是它的“商业性”比较强,或非常强。
商业性的畅销有自己的必要条件,它往往形成这样几个特点:
它不能太有艺术上的追求;不能太有个性;不能太深;不能太新;要合于大众口味,要趋于“平均值”;另外,成本不可太高(最好能快速成书,前一本销售势头刚过,下一本随即接上,就像一张接一张连续发传真似的)。
显然,在创作上,它与作家在审美价值上的追求走的不是一条道。其结果,使之更接近于电视剧,而不是电影――看电视剧可以不用心,可以吃零食并闲聊,可以分心开小差,甚至走开一会儿再接着看,它可以让更多的人轻松接受;但看多了电视剧的人,再看高质量的电影会很不习惯,以至于看不懂了。或者也可以说,它更接近于大众快餐,更像肯德基、麦当劳。
商业童书将会大量出现,甚至占领童书市场的大半个天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现在的出版社已是企业,企业是要经营的,资本总是要扩张的,这是它的本性。所以,多家出版社争出杨红樱或类似杨红樱的书,也是正常现象,是不必劝阻,也无法劝阻的。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是商业行为,是盈利。出版者不必遮遮掩掩,也不可上欺下瞒,明明是迎合市场的快餐,却偏要自诩为“最佳烹饪作品”。出版社可以理直气壮挣钱,但要实事求是宣传。这是底线。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宣传机构、专业团体、研究者、专家、教授……对此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再不可把商业童书误当作优秀文学作品推荐给我们的儿童了,儿童的读书时间非常有限,高品质的非盈利性的儿童图书市场因受到商业童书的挤压正变得越来越小,我们所需要推荐和奖励的恰恰是那些非商业性的好书!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真正优秀的中外儿童文学已暂时处于“弱势”的地位,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严峻的现实。对于“商业童书”,如掉以轻心,早晚会有大的教训。
当然,商业童书拉动了图书市场,完成了利润指标,出版领导部门可从产业的角度予以表彰,税务系统也可作为纳税大户进行奖励;一旦它的格调过于低下,出现了类似“三聚氰胺”那样的有害成分,政府部门则应予以处罚或绳之以法。总之,要依法办事,决不能再将其商业上的拳头产品与文学艺术上的高端作品混为一谈了。
真正危险的,是资本不但有扩张的本性,还有强烈的垄断欲望。
在北师大的会上,几家出版杨红樱商业童书的企业已联起手来,除公布一些夸张的数据以说明杨的书占领市场份额之大,以对别的书籍和出版社形成威慑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呼吁批评界应该改变批评标准了。换言之,就是要以杨红樱的书作为评价一切儿童文学的基准,而其理由,就是畅销。
这里传达出的信息,是一个书业“托拉斯”的雏形已在蠢蠢欲动。托拉斯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之一,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托拉斯的成立,是为了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反垄断法”的时候,必须警惕这种“垄断销售市场”的行为。因为它一旦形成,中国的童书市场事实上也就形同荒漠了。商业垄断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具有同样的破坏力,它们最害怕的就是百花齐放。
郑重提出“反思童书评价体系”的命题(见2008年10月15日《中华读书报》)。事实上,所谓“严肃的儿童文学评论体系”,虽不是一成不变的,却也不是能够轻易修改的。儿童文学评价体系的背后,是整个世界儿童文学史和无数优秀作品在作支撑。试问,杨红樱的那些商业童书真的足以推翻世界儿童文学史和无数已有的优秀创作么?更大的问题出在对批评的定位上。本来批评是外在的声音,一如品酒师之于酒商的酒。但郑重以“小读者着迷”(其实也就是卖得好)为由质疑“评论体系”,要让评论体系向卖得好的书靠拢。一旦评论真的不再以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为基准而只以当下最畅销的书为基准了,那还会有别的声音吗?批评就变成了畅销书自己对自己的表扬和对异己者的讨伐。从此,“当下最畅销”的也就成了永远的霸主,这不就是垄断的形成吗?
从“商业童书”的悄悄产生,到人们还未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却围绕它发生了种种争论,再到它迅速攫取出版资源,并一步步谋求垄断,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我们再也不能懵懵懂懂,不予认真对待了。
(本文编辑:陈学勇)
